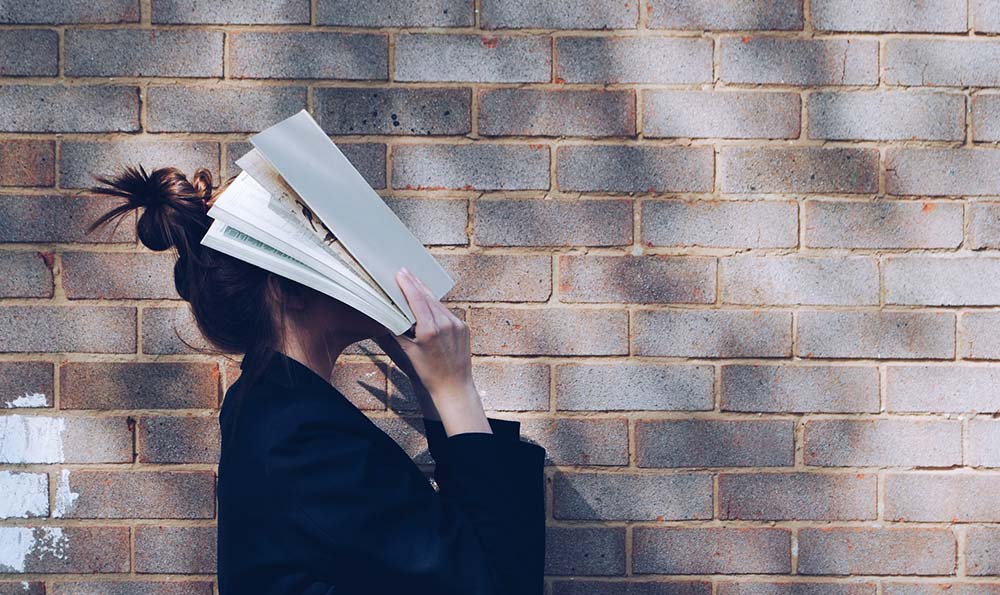清晨的台北巷口,90岁的高秉涵正对着镜子系领带——领口别着枚褪色的铜扣,是母亲1948年给他缝在棉袄上的。行李箱放在脚边,里面裹着两坛用红布扎紧的骨灰,这是本周要送回江苏盐城的“老陈”——去年冬天,老陈攥着他的手说:“秉涵,我老家的油菜花该开了,帮我闻闻味儿。”

30多年来,这样的“快递”他送了100多回。行李箱换了6个,红布用旧了20块,每一次跨海峡的飞行,都像在替谁“补”一场迟到的团圆。

1948年的冬天,13岁的高秉涵攥着母亲塞的窝窝头,挤上厦门到基隆的船。母亲在码头的风里喊得嗓子哑:“儿啊,活下来!娘等你活着回来!”那声音裹着菏泽的寒气,跟着他漂过海峡,成了他在台湾最烫的“解药”——饿到啃树皮时,想起母亲的话;被同学欺负躲在巷子里哭时,想起母亲的话;甚至在台北医院的病床上,他都攥着那枚铜扣:“我要是死了,娘就白等了。”

1979年,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母亲写了封信。信封上的地址是“山东菏门外李家庄”,贴了8张邮票。等了半年,回信终于到了,却只有一句话:“母已于1978年秋病逝,临终前还喊着你的名字。”那天晚上,他把自己关在书房,把母亲的信贴在胸口,哭到台灯的光都凉了:“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,她等了我一辈子啊。”

1990年的同乡会,几个老兵抱着他的腿哭。“秉涵,我们这把老骨头回不去了,你最小,以后要是能回家,把我们的骨灰带回去吧。”那天夜里,他翻出自己刚拿到的返乡证明——1991年春天,他终于要踏上离开43年的故土。当他抱着第一个老兵的骨灰站在菏泽村口时,老兵的女儿“噗通”跪下,手里举着一碗温热的小米粥:“叔,我爹生前总说,想喝口老家的粥。”那一刻,他突然懂了:这些骨灰不是坛坛罐罐,是老兵们藏在枕头底下的“老家地图”,是病床上念叨的“村头的老井”,是中秋夜对着大陆方向摆的那副空碗筷。

去年清明,他在母亲的坟前烧纸。风把纸灰吹到他手背上,他摸着墓碑上的“李氏”二字,声音轻得像落在花瓣上:“娘,我带了100个老伙计回家,你要是见到他们,帮着认认乡亲。”现在的他,耳朵有点背,却能听清电话里大陆侄子说“家里的玉米熟了”;眼睛花了,却能准确认出每坛骨灰上歪歪扭扭的“老家地址”——有的写着“河南安阳西郭村”,有的画着棵子树,有的只写了“大陆”两个字。
有人问他:“高老,你累吗?”他笑着拍了拍行李箱:“我娘等了我一辈子,这些老伙计等了半辈子,我多走几步,他们就能早一天‘闻见’老家的味儿。”
90岁的高秉涵还有个心愿。他想活着看到两岸的高铁通到台北,想带着孙子去菏泽吃母亲做的手擀面,想告诉那些已经“回家”的老兵:“咱们的家,再也不用隔着海算了。”
风从海峡那边吹过来,带着他未改的山东口音,吹过台北的老巷,吹过菏泽的老槐树,吹过每一个等着“回家”的人心里——就像母亲当年的那句话,从来都没凉过。